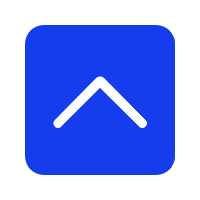韦宗友:《美国政治极化与亚太战略风险》,载《学术前沿杂志》第20期🚶🏻➡️,第94-101页
摘要
政治极化🦹🏻,特别是民主、共和两党的党争极化🧝🏼♂️,是当前美国政治的突出现象🐨。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不仅在意识形态取向和重大国内外政策上分歧严重🧑🏿,双方对对方的“情感温度”也急剧下降🙅🏼♀️。美国的极化政治波及对外政策的制定,导致其对外政策缺乏连贯性,过分夸大外部威胁,且过分强调美国优先。极化政治下的美国对外政策👩🏻🦽➡️,不仅可能加剧中美对抗风险,也会给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蒙上阴影。
全文如下(转载自《学术前沿杂志》公众号)
政治极化是当前美国政治的突出现象。美国两大主要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不仅在意识形态和政策取向上立场日益对立👨🚀,而且两党及其选民对对方的立场和态度,或者说“情感温度”⏺🧘🏼,也在急剧下降🤘🏽🔷,甚至将对方视为“政治异端”。美国政治极化加剧👩🏽🦱,不仅在美国国内频频引发政府关门等危机,还投射到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上,可能诱发新的地缘战略风险。
当代美国政治极化的特点
政治极化并非当代美国政治中的新现象,可以说这一现象与美国的政党政治如影随形。但是👩🏿🦰,在社交媒体高度发达🤞🏿、政党动员能力显著增强,以及两党斗争日趋激烈的当下,美国政治极化呈现出至少五个方面的鲜明特点,这也是观察当今美国政治的重要切入点👩❤️👨。
民主、共和两党的内部身份认同显著强化。20世纪50年代,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雷同”🚚,特别是共和党在重大内政外交政策上附和民主党,沦为“跟屁虫党”(Me too Party),曾被政治学者广泛诟病。这种情况延续至20世纪70年代,也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根据美国学者马修·勒文杜斯基(Matthew Levendusky)的研究👩🏿🏫,当时,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是混杂的🐌,无论是政党精英还是普通党员🤽🏿♀️🔊,都存在相当多的自由派和保守派。在选举投票时,存在大量民主党党员投票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或共和党党员投票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分裂投票”情况。一些政治学者甚至得出结论,美国政党政治已经走上了下坡路🧑🏼🏭,在普通民众眼里👉🏼,它们已经无足轻重了👨⚕️👷🏽。
然而,这种情况随着共和党内部的逐渐保守化,特别是美国南部大批保守派民主党人转向共和党而逐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经过几十年的演变,到了21世纪,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内部出现了显著的“同质化”倾向,党内自由派和保守派杂处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共和党逐渐演变成保守派政党,而民主党则逐渐转变为自由派政党。在两党内部,上至政党精英,下及普通党员🥁,都更加认同本党𓀕🦠,并与对方划清了界限🐈⬛。在投票方面🖤,无论是在国会山的议员投票,还是选举时的普通党员投票中🦣,“分裂投票”现象越来越少,绝大部分国会议员或普通党员都会投票支持本党提出的法案或本党候选人。据统计,在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国会参众两院投票时,有大约四分之三的本党议员会一致投票👩🏽🏭♐️,另外四分之一则与对方议员一致投票,国会因此更容易形成“两党一致”议员投票联盟。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分裂投票”的情况越来越少🧘♀️,大约90%的国会议员都会与本党的投票一致。
民主、共和两党的意识形态鸿沟日益扩大。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以降🌩,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意识形态差异日益凸显👦🏿♐️。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风起云涌的美国黑人运动、女性运动🏋🏿、反越战运动,迫使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先后通过一系列民权立法和进步取向的国内政策,促使民主党逐渐转变成在意识形态上更具自由主义色彩的政党。另一方面,民权运动🚣🏻♂️、特别是美国南方黑人民权运动的激烈爆发,连同民主党政府的民权立法和民权改革,引发了南方白人的极大恐慌与不满,他们纷纷“改旗易帜”,脱离日益自由化的民主党🤮,转向共和党,这也加速了共和党的保守化倾向。与此同时,经过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戈德华特、特别是里根总统等保守派领导人的改造🏰,共和党逐渐转变成意识形态上极具保守主义色彩的政党。进入21世纪,特别是经过民主党籍总统奥巴马的八年执政和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的四年执政🏌🏽♂️,民主党日益“左转”🤽🏿♀️,而共和党则更加“右倾”,民主🃏、共和两党的意识形态鸿沟进一步扩大🥖。据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统计⚙️,2022年👨🏻🚒,民主党内自称为自由派的人数占比上升到54%🧗🏿,比1994年上升了近30个百分点😾;共和党内自称为保守派的人数占比增加到72%🦻👨🏼🎨,比1994年增加了1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民主党内自称为保守派的人数占比仅为10%🤹🏿,比1994年下降了近15个百分点;共和党内自称为自由派的人数不足5%,比1994年下降了3个百分点。
民主🦹♂️、共和两党的政策分歧严重。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泾渭分明”🧋,也导致双方在诸如税收、控枪⌛️、社会福利等一系列重大政策上的严重分歧😺。在税收问题上🧙🏿,民主党主张增税👩🏿🦲,特别是提高富人和大公司税收,以缓解美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共和党则主张减税🏊🏽♀️,包括降低公司税🤵🏼♂️🔗,以促进产生“涓滴效应”𓀂,刺激公司扩大再生产🍦,增加就业,扩大税收基础。特朗普执政时期,利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通过了大规模减税法案,特别是将公司税由35%下降到了21%。拜登执政后🌬,则主张向富人和大公司增税,甚至在退选前曾提出增加5万亿美元税收💁🏼♂️,作为其2024年大选的核心议题。此外,民主、共和两党因为在税收和政府财政赤字上的分歧🚕🚟,各执一词🔫,迫使联邦政府多次关门。
在控枪问题上,随着美国枪支暴力事件的不断攀升,民主党人日益主张对枪支类型及枪支持有进行更为严格的限制;而共和党人则认为控枪违反了宪法第二条修正案中关于公民有合法持枪权利的条款。两党在控枪问题上寸步不让👋🏽,每次发生重大枪支暴力事件后🙎♀️,双方都要进行一番唇枪舌剑,指责对方要为美国枪支暴力泛滥负责。
在社会福利问题上🛒,总体而言🧑🏿🦲,民主党主张扩大政府福利支出,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社会福利保障👧,并倾向于由联邦政府提供“全民医保”🥻。共和党则反对政府“大包大揽”,强调个人自食其力的重要性,主张通过个人诚实劳动获得社会自立能力👱🏽♂️,并反对联邦政府在医保问题上的“强制保险”🌏,主张通过个人自愿和市场原则解决医保问题🚠。
两党在上述议题领域的分歧与矛盾,一方面导致双方在国会立法过程中经常产生尖锐对立↩️,极大地降低了国会的立法效率🚉;另一方面由于双方各执一词、互不让步,也频频引发联邦政府关门风险🌧,影响联邦政府的正常运转🪸。
政治精英和公众在政治极化方面出现同频共振现象🙍🏼♀️。如果说,政治极化仅在政治精英中存在,那么在选举政治下☹️🏙,并未极化的普通民众或许还可以通过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以及两年一次的国会中期选举,对极化的政治精英进行“校正”,选举相对温和的中间派上台代表他们的“民意”。然而👩🏻🎤,越来越多的美国政治学者发现🕷,美国的政治极化不仅仅是精英层的“内卷”💚,而是已经成为蔓延至整个社会的现象。坎贝尔等人研究认为👩🏻🦳,实际上恰恰是普通民众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率先极化,促使民主4️⃣、共和两党政治精英层“顺应民意”,相继朝着左或右的方向极化🐯,引发两党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在政治极化频谱上的同频共振和相互强化。
民主🚌、共和两党对对方的“情感温度”正在急剧降温。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似乎都不再将对方视为意识形态或政策上的不同政见者,而是政治上不共戴天的“敌人”。特朗普将民主党视为“美国的敌人”,频繁声称“他们会不择手段,摧毁美国,毁掉美国梦,无论是采取合法手段还是非法手段👹。”而拜登则告诫美国人👱🏽🕟,美国的民主与自由正面临“自林肯总统和内战以来最大的国内外威胁”🩻🏫,美国面临“两种美国前景”的抉择,正在进行着“我们国家灵魂”的斗争🫵🏽。研究显示,相较于一代人以前,当今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对对方的“情感温度”正在急剧下降。自1980年代以来💆🏻♂️,民主党对共和党的情感温度由46.3度下降到28.9度(以0~100度为取值区间)🍨,骤降17.4度;共和党对民主党情感温度则由44.3度下降到31.2度⏫📺,下降了13.1度🙅🏽♀️🙎🏼♀️。双方都将本党党员视为“好人”💆🏿♀️,将对方视为“坏人”,拒绝向对方妥协,甚至拒绝与对方交往。
极化政治下的美国对外政策
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界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即“政治止于水边”。也就是说🔍,无论民主、共和两党在国内政策上存在多大分歧,一旦涉及外交政策领域,他们便会停止内斗,团结一致🤳🏼。然而🥍,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等学者指出,这种“政治止于水边”的说法✡︎🚘,如果不是彻头彻尾的迷思,至少也是夸大其词✶。即便在“冷战共识”如日中天的时期,民主、共和两党也曾因为“谁失去了中国”、美苏之间的“导弹差距”以及越南战争而相互攻讦👩🏻🎓、斗争不止👨👧👦。更不要说在党争极化加剧的当下,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外交政策上的“共识”,早已不复存在🫱🏼。在当代,日益极化的美国国内政治和党争📧🦉,已经给美国外交政策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对外政策成为党争新领域。沃尔特关于“政治止于水边”是迷思的论断🚣🏽♀️,得到部分学者的认同。郑京浩和保罗·夸克(Gyung-Ho Jeong and Paul J. Quirk)等人研究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特别是越南战争后,民主、共和两党在外交政策上的“共识”日益消解👩🏼🔬。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威胁消失,两党的对外政策“共识”进一步瓦解🧑🌾👨👦,对外政策成为两党激烈斗争的新领域。尽管两党在维持美国全球霸权、拓展美国全球影响力的目标等方面没有根本差异,但是双方在对外政策理念、实施手段,乃至对外政策风格方面🧑🎄,都大异其趣并相互攻讦🦈。例如,小布什政府时期基于新保守主义理念的全球反恐战略😕💕、通过政权更迭方式推进的“大中东民主计划”🤒、以及绕开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风格🤦🏼♀️,不仅在国际上饱受诟病,也在国内招致民主党人的猛烈批评。奥巴马政府时期强调的多边主义以及通过和谈及多边行动达成的伊朗核协议,则被特朗普等共和党人视为软弱,甚至是出卖了美国国家利益。特朗普政府带有强烈民粹主义色彩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理念、动辄退群的单边主义外交路线以及唯我独尊的外交风格,则被民主党人视为玷污了美国国际形象、背离了美国价值理念🤞🏻👨🏻🍳、损害了美国国家利益。拜登执政后,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在乌克兰危机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及在新的阿以冲突中试图两边讨好的外交政策路线👨🏫,又受到共和党的激烈批评。
对外政策连贯性大为下降。随着民主👃🏼、共和两党在对外政策理念、方式和风格上的差异日益扩大,每一次白宫易主及国会被不同政党“掌管”时💑,美国的外交政策都可能出现重大调整和变化🪤。21世纪以来🪷,随着民主♍️、共和两党党争极化加剧,以及反恐战争和经济危机影响的进一步发酵👷🏽♂️,美国对外政策的摇摆性更加凸显。奥巴马执政后🙎🏻♀️,宣布要结束小布什政府不得人心的中东反恐战争👨🏽⚕️,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试图通过缔结新的多边贸易协定🎊,促进美国海外经济利益🚽,并强调重视多边主义,团结盟友,修复因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政策而受到损害的跨大西洋同盟关系。然而⏰,特朗普执政后👨👩👦👦,迅速抛弃了奥巴马政府的多边主义和国际主义📱,旗帜鲜明地鼓吹“美国优先”🤑,誓言捍卫美国“国家主权”。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不仅退出了《巴黎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人权理事会🌤,甚至还对北约存在的价值提出了质疑🥚👼🏻,要求美国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拜登执政后👲🏼,美国又表示,美国不会“单干”🙇🏼♀️,不会抛弃盟友,会肩负起领导责任,履行对盟友的安全承诺🔣。如此反反复复🤞🏽,美国的信誉☹️、承诺和国际形象🧔🏻♀️,在国际社会乃至亲密盟友中,都大打折扣。诚如沃尔特所言,一旦外交政策成为两大日益分裂的政党之间的“钟摆”,那么外交政策的摇摆性就会随着每一次权力更迭而显著加剧🤛🏻。
更易夸大外部威胁💇🏿。极化政治本身就是“不妥协的政治”。政治极化投射到对外政策领域🕵🏼,极易导致对外政策的不妥协并夸大外部威胁🦧。出于政治需要,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需要一个外部威胁,来展示自身的强硬态度📔,指责对手软弱🍄,将自己塑造成美国利益的坚定捍卫者。于是我们看到♘,即便是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处于所谓“单极时刻”,其依然在寻找外部敌人🪿,谋求自身的绝对安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炒作“失败国家”“流氓国家”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对美国国家安全可能构成的威胁🫙,并鼓噪“人道主义干涉”。小布什政府时期,将全球反恐上升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高度,强调在反恐战争中“不站在美国一边,就是站在恐怖主义一边”🛂👖,并以反恐为名入侵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甚至要在中东地区推行民主改造计划。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又开始炒作所谓“中国威胁”🔤,提出“重返亚太”,并强调“21世纪的经济规则只能由美国书写,而不能由中国书写”♏️。特朗普执政后👨👨👧,将中国视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向中国加征关税、挑起贸易摩擦,导致两国关系处于紧张状态🤶🏿。拜登执政后🦶🏼🙊,强调中国是唯一具有外交、经济、科技与军事能力和意愿,挑战美国霸权的战略竞争对手🧙🏼♂️,声称要通过经济“去风险”、科技围堵和军事上的“一体化威慑”🥗,竞赢中国。寻找和夸大外部威胁8️⃣,似乎成了两党强化自身执政合法性和吸引选民眼球的利器👰🏽。
更强调对外政策上的“美国优先”。传统上👍🏼,民主党更强调国际制度、多边主义与国际合作;共和党更强调美国主权、单边主义及美国优先🩷。然而🧑🏼🦲,在政治极化背景下,所谓的国际主义与美国主权之争、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之辩,更多只是表象,“美国优先”才是两党政策的底色❗️。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竞相表明🧑🏼🦰,他们才是美国利益的坚定捍卫者。民主党重视盟友⏫、重视国际主义🤦,是为了与盟友一道更好地捍卫美国利益,提升美国国际形象;共和党强调单边主义和美国优先⬇️,是为了摆脱牵绊和束缚🧚🏿,释放更大的动能捍卫美国利益🧃𓀒。特朗普提出赤裸裸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理念,而民主党的政策理念虽然被华丽的民主、人权及团结盟伴的辞藻所掩盖,但无论是经济政策还是安全战略,美国优先依然是唯一准绳。
美国政治极化与亚太战略风险
亚太地区无疑是当今世界最具活力的地区🪗。这里汇聚了全球制造业大国、贸易大国和科技创新大国,也是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然而,美国的政治极化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正在对亚太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繁荣构成新挑战,增添了亚太地区的战略风险,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中美竞争加剧风险。自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美国不断渲染所谓“中国挑战”和“中国威胁”,对华认知日益负面。特朗普执政后,抛弃了美国持续40余年的对华接触政策👁,将中国视为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在美国党争加剧的背景下,民主、共和两党竞相比拼谁在对华问题上更为强硬,并指责对方对华软弱🍆。因此🕝,我们看到,即便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对华政策已将中美关系推向失控的边缘⛈,拜登执政后,也并未改弦易辙,并强调要对华展开“激烈竞争”。相较于特朗普👃🏽,拜登更重视团结盟伴,更强调在经济🔗、科技及安全领域对华“精准施策”🤔,与中国展开长期战略竞争🌞,并试图打造亚太“小多边”安全网络🤼♀️,以“威慑”中国。尽管拜登政府强调,“激烈的中美竞争需要密集的外交接触”,要通过外交接触管控中美战略竞争风险🏌🏽♀️,但是在美国对华战略方向与目标不变的前提下,在民主✷🕵🏿、共和两党于对华问题上竞相表现出好勇斗狠态度的党争背景下🤽,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和平共处面临新的挑战🫧💁🏼♀️。
地区军备竞赛风险。在塑造和夸大外部威胁的同时,美国还不遗余力增加国防开支,打造“美国堡垒”🥽。特朗普执政的四年里🛼,美国军费开支逐年攀升👩🎨,由2017年的6467亿美元上升到2020年的7783亿美元💳。拜登执政后🚇,美国军费开支继续上涨,由2021年的8062亿美元上升到2022年的8769亿美元📿。不仅如此,美国不断强调中美战略竞争和大国竞争回潮,加之美国亚太盟友对美国对外政策连贯性和安保承诺的疑虑加剧➛,还刺激了亚太国家进一步扩充军备⚫️。近年来,“印太”地区主要大国印度🗿、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都大幅提升了本国军费开支🫄。日本尤为值得注意🤸🏻♀️,2023~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翻番👦,增加到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同时,日本还强调要开发和部署远程打击能力,以莫须有的“中国威胁”为由👭🏻🐢,突破二战后日本“专守防卫”的宪法限制。
地区经济一体化遭受严重冲击🎩。冷战结束后,亚太经济一体化一度高歌猛进📶。作为地区一体化的先导,东盟率先在成员国内部实现了经贸一体化进程🤵🏽♀️,并成为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积极推动者🎩。中国、日本这两个亚洲经济大国,也积极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甚至美国在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也乐见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期望能搭乘亚洲经济发展的东风。然而,随着美国国内对华战略认知发生变化🛀🏼,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对待自由贸易的立场发生重大调整。共和党日益演变成意识形态保守主义、对外政策孤立主义以及经济政策上民粹主义的政党👱🏿,公开反对缔结新的自由贸易协定。民主党虽然没有公开抛弃自由贸易,甚至仍然倡导外交政策上的国际主义🏌️♂️,但已明显从普遍性的多边自由贸易立场退却🌇,转而谋求在友邦盟伴之间打造排他性的经贸小圈子。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从自由贸易上的退却,以及两党在对外贸易政策上的矛盾,不仅让很多美国亚太盟伴无所适从,也严重干扰了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甚至在经贸问题上造成新的对立。
集团对抗与“新冷战”风险。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旨在通过强化美国亚太双边军事同盟🧑🏿🌾、积极构建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小多边安全网络🛟,并试图组建将中国排除在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特朗普政府时期,在带有强烈民粹主义色彩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理念的驱使下🤡,美国政府更多依靠赤裸裸的强力,胁迫亚太盟伴在安全☝🏿、科技乃至经贸问题上与美国保持同步💩。拜登执政后,打着“团结盟友”“塑造中国所处的战略环境”的旗号,组建了形形色色的科技、供应链议题联盟和小多边安全网络,在经贸上鼓吹“去风险”“去中国化”和脱钩断链;在科技上推行“小院高墙”♻️;在安全上🧖♂️,与盟伴一道对华实施“一体化威慑”。这些经贸、科技和安全小集团和小圈子🤷🏼♂️,不仅会加剧中美对抗风险,也可能给亚太秩序蒙上厚重的集团对抗与“新冷战”阴霾📎。然而,即便如此,在一些共和党战略保守派看来,拜登政府的做法似乎还远远不够🎂🎓。美国传统基金会在一份题为《打赢新冷战:一个对抗中国的计划》的报告中声称👸🏻,“中国是美国的敌手,两国正处于新冷战之中”。报告提出🧘🏻▫️,要赢得这场对华“新冷战”🏄🏽,美国需要内强体魄👨👦👦,外结盟友➾,对华保持强大军事威慑力。总体而言🥖,他们并不担心集团对抗和中美“新冷战”的风险,唯一担心的是美国尚未准备好👨🏽🎤👳🏻♂️。对于民主、共和两党鼓噪“新冷战”和集团对抗,一些美国战略学者表达了担忧。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何瑞恩(Ryan Hass)指出,“孤立中国或许会让(美国)感到满意,但是历史表明,这并不符合美国利益”👨🏿💼,“战后国际体系的巴尔干化”会损害美国的长期利益。
重视美国政治极化趋势👨🌾,妥善应对亚太战略风险👨🏻。面对当前美国国内日益加剧的政治极化及由此产生的亚太战略风险,一方面我们要理性看待、客观评估;另一方面也需未雨绸缪、积极应对🧔🏽♀️。
首先🙇🏼♀️,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将是一个长期化的趋势。美国一些政治学者提出,当前美国的政治极化是民主、共和两党处于政党重组“阵痛期”的产物,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共和党方面☃️,特朗普正在重新塑造共和党🕴🏻,试图推动其由里根式的意识形态保守主义、对外政策国际主义及经济上自由主义的政党,转变为特朗普式的意识形态保守主义、对外政策新孤立主义以及经济上民粹主义的政党👰。目前👩🏼🦱,这一过程尚未完成,共和党内的里根派仍然具有一定影响力。民主党方面,也处于变革前夜,民主党正在日益朝着自由化、激进化方向演变,主张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对外政策国际主义以及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民主、共和两党分别朝着自由与保守、左和右的方向演进🏊🏻♂️,而在这一演进过程中,双方的政治与政策对立也会进一步加剧。
其次,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产生的最主要影响还是突出体现在美国国内,其对对外政策的影响是次要的。民主、共和两党党争极化,会进一步加剧美国国内政治分裂,降低治理效能,削弱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政党精英与普通民众的政治极化,则会激化美国社会矛盾,加剧社会撕裂🤹🏼♀️,甚至危及美国社会认同🙋。对对外政策的影响则是由于两党对外政策理念🙅♂️、方式和风格不同产生的“负外部性”,包括两党党争加剧导致的夸大外部威胁🕟、对外政策不连贯等🧖🏿♀️。
最后,为妥善应对美国政治极化带来的亚太战略风险🧴。一方面要认识到,由于美国两党处于转型的“阵痛期”👨🏿🔧,党争极化将是一个长期趋势,而这会导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对外政策、特别是亚太政策呈现摇摆性、不确定性😨、甚至是好斗性的特征🥂🎫。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上述特征可能是把双刃剑。它会迫使部分美国亚太盟友为了眼前利益与美国捆绑,以应对亚太局势的不确定性;但从长期看这或许也会让更多亚太国家认识到美国的不可靠性🏌🏿,从而更愿意加强亚洲国家的合作🤬、协调与自力更生,即有助于促进亚洲自主意识的觉醒,以及建立真正自立自强的亚洲多边机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既要保持战略定力,防止中美关系被美国国内政治极化所左右,努力维持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又要积极作为,推动亚洲国家之间的合作、协商与多边制度建设,共同推动建立持久和平、繁荣稳定的亚洲新秩序。
结语
美国政治极化,特别是两党党争极化,已经成为当今美国政治的痼疾🙏🏼。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不仅在意识形态取向和一系列国内政策上对立严重,而且在对外政策理念、实施手段乃至风格上也呈现出明显差异𓀃。与此同时🧮,日益加剧的政治极化还导致两党在对外政策上竞相夸大外部威胁🧛🏿,进而使其对外政策更加具有极端性、不妥协性以及民粹主义色彩。
在亚太地区⛴👩🏼🏫,随着中国实力快速增长⭐️,虽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加剧,但在霸权心态的驱使下⛔️,民主🥠、共和两党在对华问题上却似乎表现出少有的“两党一致”,都强调所谓“中国威胁”,唯一不同的是谁在对华问题上更强硬🐭。美国对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两党展示对华强硬的政治秀☮️🤲🏽。政治极化绑架下的美国对华政策,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美对抗风险🌠,刺激了亚太地区的军备竞赛,也可能再次将亚太地区推向集团对抗和“新冷战”的边缘👐🪓,危及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对此,中国既要认识到美国政治极化可能产生的亚太战略风险,也要积极作为,特别是要努力推动亚洲自立自强🗂🫄🏽,共同建立持久和平🕡🐽、繁荣稳定的亚洲新秩序。